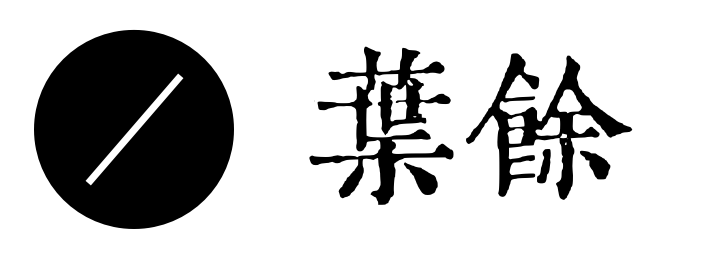我还在开会的时候,接到弟弟的电话,说母亲走了,我没有想到这么快。春节期间,我们在成都过年,和母亲视频交流的时候,感觉她还好好的。我匆匆订票回到了山东老家。
母亲名字叫何乃香,和我父亲是一个村。我们村子的名字很好听,西楼。不过它的名字不是来自月满西楼的婉约意境,据传乃是因为何姓村民修建的一个地主庄园的阁楼或是碉楼,所以叫何家楼,后来一部分人迁到了东边,迁过去的叫东楼,何家楼就称为西楼。到今天,楼早已经不在了,但原来楼所在位置的附近,至今仍然有个约定俗成的称呼,叫“楼底”。我母亲就出生在楼底那个范围内。
我姥姥很早就去世了,去世的时候,母亲也就只有两三岁。姥爷一个人带着母亲长大。生活当然是很艰难的。正常的人家都艰难,更何况是他们。后来她嫁给同村的我父亲,刚开始的时候日子也很难。后来我父亲开拖拉机,后来又贷款买了一辆拖拉机跑运输,生活才开始好起来。
好景不长,1987年,父亲在一次意外中丧生,那年母亲35岁。我在今天以四五十岁的年龄去设身处地想一下,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。大概从那时起,她的哮喘病开始严重起来。后来,我继父和母亲结婚,入赘来到了我们家,继续支撑我们的家庭。母亲先是生了一个妹妹,这个妹妹不到半岁就去世了,后来生了我弟弟。
我从初中开始住校,在家的时间很少。初中还有点假期,到了高中,一个星期也就只有半天能回一次家。我对母亲的记忆非常琐碎。小的时候经我常问她关于我出生的故事,她就跟我讲,怀我的时候,姐姐不满三岁,我是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,所以她就逃跑,跑到她的姨家去躲着。那些细节我到现在也记不清楚了。不过这些故事,也导致我看《超生游击队》这样的节目,笑不出来。挺着肚子到处躲藏,担惊受怕,怎么会是一个喜剧呢?
还有一些艰难的场景让人难忘。有一年,我的姨姥,也就是母亲的姨妈来看她,看到我在,给了我十块钱,我上小学,没见过这样的大钱啊,送走姨姥之后,就带着那十块去上学了,母亲追了我近两里路,把钱抢回去了。想想又心酸又好笑,母亲那时候身体还好。
母亲识字不多,对我们的教育也很简单而细碎。在村里,何姓是个大姓,她的辈分很小,导致我们出去见到个人,就是舅舅、姨、姥姥、姥爷这种级别的。母亲教育我们,要尊敬长辈,见个人就要打招呼叫人,不能因为年纪小就不称呼他们。我上初中上高中了,就念叨我好好学习;上大学了,就让我们好好交朋友,别惹呼人。我工作了,就叫我好好工作,团结同事。我结婚了,就跟我说,别打架,嘴甜儿点,对人家好。
我没有更多的回应,只有答应。我和母亲的共同的话题很少,她所知道的街坊邻居、七亲八戚的事情,我因为在外面,知之甚少。我的工作和社交圈子又没有办法和她同步。每次回去时候,基本上就是她说着,我听着。我知道她关心我,我也只能跟她说,我很好,你放心吧。
这十几年,母亲身体一直不好,哮喘导致肺部的问题,又发展为肺心症。我继父、弟弟和我姐在家把她照顾得非常好。母亲出生在1952年,按老家虚岁的算法,她过完年就是74岁了。如果没有他们含辛茹苦地照顾,她可能也不会多活这好多年。
2022年8月,母亲又一次病重,到日照的人民医院住院,按弟弟和姐姐的判断,她的状态很不好。那时候疫情方面管理很严格,我好不容易进了医院,跟她交流,她还认得我。住院期间,我太太告诉我,她怀孕了。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。可能是个巧合,她挺过来了。出院的前一晚,我还到书奇家住了一晚,他们的小K还出生不久,他们还借车给我,让我送母亲从日照回五莲。
也就是那一次,我向她再一次传了福音,和她一起做了决志的祷告,她跟我一句句地念。
“亲爱的耶稣,我承认我有罪,我需要你,你为我在十字架,牺牲了你自己,救了我的生命。我愿意忏悔,有永远的生命,奉耶稣的名祷告,阿们。”
我还告诉她无论什么样的艰难的境况,要向耶稣祷告,说耶稣救我。我说这样将来有一天,我们会在天上见。只是我对本地的教会一点也不熟悉,母亲没有后续的牧养和跟进,也没有受洗。只有我每次回来,跟她聊一下我们的盼望和归宿。
母亲去世,我心里还在想,有没有可能请日照的教会帮助做一个基督教的葬礼。回家一看,弟弟和姐姐已经安排好了,基于强大的文化压力和对他们的敬重,我只能听从他们的意见。但是我心里知道,我有一个盼望,就是我相信母亲因为她口里承认,心里相信,就必得救。

村西边有一条岭。送完葬的第二天,天气很好。我在平房顶上拍到了落日的余晖,我看到太阳还悬在西岭上,我开车想到那里再拍一张。可是仅仅几分钟的时间,我开到那里时,太阳便已经看不见了。
小时候,我看着东边的山,西边的岭,很想知道那边是什么。我曾经走路去过东边的昆山,只不过没有爬到山顶。我也曾一路向西,最多到了满堂峪村,那里是我大姑的家,也是我在成都教会认识的曾老弟兄祖上的家。我向往外面的世界,报考大学的时候,选择了我心目中几乎最远的地方,四川成都,那时候需要坐两三天的火车才能到达。近三十年了,走过了很多路,经历过很多事。但我仍然不像我太太,对她的故乡哈尔滨充满那么多的回忆和不舍,我对一个地方没有那么多的眷恋。我只是在意一些人,人是我心里面所有的纽带。哪里有我所牵挂的人,我就向往那里。哪怕他们住在火星上,我也会觉得火星是我的家乡。
姐姐说,母亲躺着的这些年,经常透过窗子向外眺望。可能是想出去走走,也可能想看看有谁来了。我觉得特别惭愧,不能够多陪伴她。也感叹她的灵魂被限制在日渐衰残的身体中,是多么地痛苦。如今母亲睡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,但是我知道她的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,我知道将来有一天,我必然与她相见。
以此纪念我的母亲何乃香(1952.5.14-2025.2.8)。